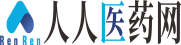白夜25周年:1998年成都的迷人时刻 天天看热讯
白夜酒吧25周年,翟永明感叹,“养个孩子到25岁可真不容易,想丢手也不是那么容易。只能磕磕绊绊,一地鸡毛,沉浮起落地使劲活下去,往下走。”
 (相关资料图)
(相关资料图)
去年,经营多年的白夜宽窄巷子店因为房租暴涨,最重不得不放弃。那时,翟永明肯定想过放弃。
但是,好几年以前,我有一次见到翟姐,跟她讲起玉林西路老店那个位置,一位朋友开了一个创意服装店“楼上的拉姆”。她眼睛里放光:玉林西路店放弃了太可惜,我还是想开回来。
后来,不但玉林西路的老店回归了,在芳华街又开了“白夜·花神诗空间”,一个更大的艺术空间,集合咖啡馆、酒吧和展览的功能,也是现在新白夜的灵魂。
估计翟姐很多次挣扎都是这样的:干脆关了算了,开了这么多年,受了这么多苦。过一两天一想,还是得坚持开下去。
小酒馆去年迎来了自己的25周岁。唐蕾也有差不多的想法。疫情三年,小酒馆芳沁店被迫停止营业9次或者10次,但是最终“不舍得”三个字,还是让唐姐坚持了下来。
它们都不是“大生意”,甚至算不上是成功的生意。它们的伟大之处在于时间,一个开25年的酒吧,安慰了多少颗孤独的灵魂啊?
去年中秋节,成都疫情严峻的时刻,一个外地乐手给唐蕾寄来了创意月饼,他写了一个纸条感谢唐姐,大意是:很多年前在小酒馆醉了一夜,第二天早上唐姐请他吃了一碗面——或许这碗面真正鼓励到了他。
白夜也是一样。每次我在朋友圈发白夜的照片,都会有外地朋友回复,回忆自己第一次去白夜的情景。
小酒馆和白夜,都走过了25年,前者是酒与音乐,后者是酒与诗歌(绘画)。毫无意外,这不仅是是成都,也是中国当代文化中最受瞩目的现象。
90年代,唐蕾在德国、翟永明在美国,接触到了发达社会的酒吧和咖啡馆文化。她们回到成都,过一段时间之后,选择了自己开一个酒吧。
这是唐姐发给我的照片。1998年,小酒馆一周年,而白夜还在筹备中,唐蕾和翟永明的合影。这真是成都的一个迷人时刻,一种新的觉醒和力量。
昨天白夜25周年庆祝,有一些白夜开业第一天就去的诗人、艺术家,也去店里祝贺。何多苓老师到场,他伸手敏捷,像一个年轻人。有一桌年轻人,看上去都是何老师的学生,何老师过来敬酒、合影,没多久,那一桌人就走了。
他们喝得很少,非常礼貌,这是2023年。而在1998年,艺术家、诗人不是这样喝酒的,从来不喝酒但是又经常参加聚会的洁尘回忆,她见过太多人喝醉酒之后的样子——在90年代的玉林街头,像她这样清醒的作家可能不多。
现在回想起来,唐蕾和翟永明先后在玉林西路开店,其实是开启了成都都市文化的一个时代:更靠近世界、和世界接轨的;更接近艺术的;更独立、更自由的。小酒馆和白夜,不仅是酒吧,也是一种价值观。它们的灯亮着,就足以让人感到温暖。
她们最初的想法非常朴素,不想去体制内上班,开一个小店来养活自己。在90年代从体制内辞职被称为“下海”,是前卫而又充满未知的生活方式;现在,人们又称考公务员、考编制成功为“上岸”,时代风尚的变化实在让人感慨。
小酒馆和白夜能够坚持,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唐蕾和翟永明这两个主理人。昨天唐姐在朋友圈留言向翟姐表示祝贺,她的话非常精准地形容了她们身上的特质:“25年前的我们已经不年轻,现在我们也没老。”
25年前,她们获得了人最重要的品质,独立和自由,这种发现让她们“成熟”,也让她们勇敢。而在今天,很多人都和时代的浪潮一样退去,而她们的内心却没有变化,她们比一些青年更“年轻”。